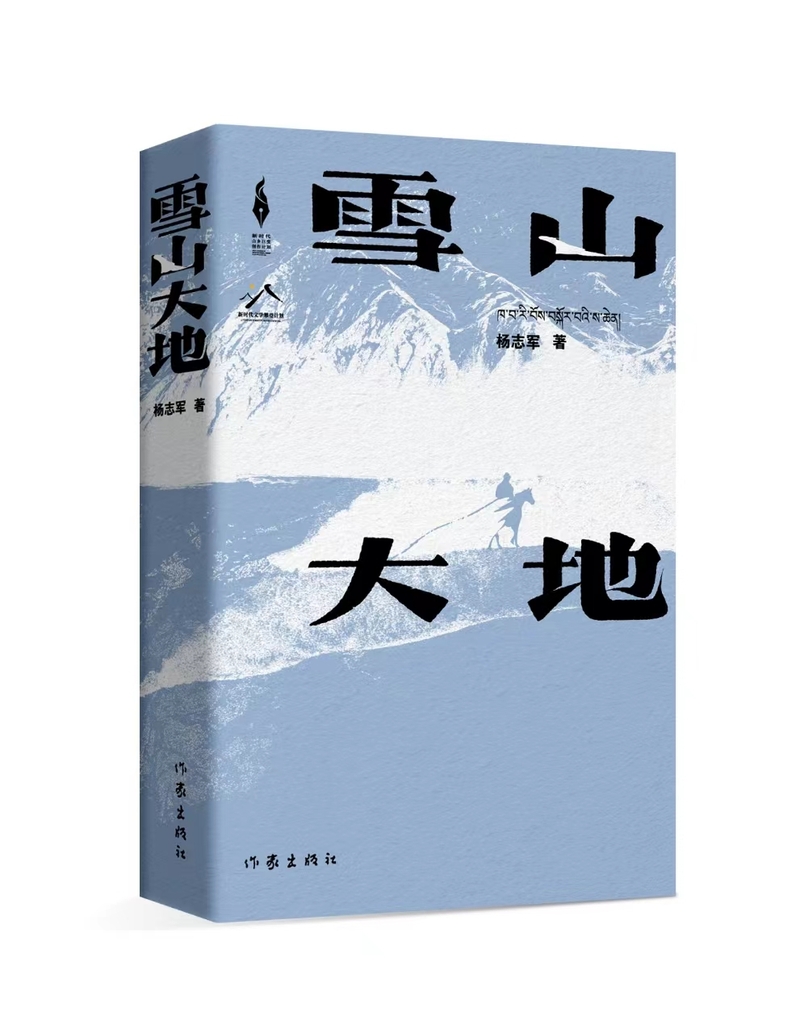《雪山大地》获选第11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杨志军很平静。只是,接踵而来的采访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但面对每一个采访者,他都认真地回答问题,哪怕很多是重复了很多次的问题。
认真是他的习惯。
他曾在雪山大地之间认真地生活;离开之后,他认真地创作《雪山大地》。他在作品中认真地追寻父母亲与共和国数代建设者的艰辛足迹,认真地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认真地注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农牧文明与城市文明间的融合与冲突。
对话杨志军,我们不仅将目光聚焦于这部获奖作品,更与作家一起,畅谈关乎文学、创作、理想的种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作家如何定位自身;面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文学提供怎样的路径以重树现代人的信仰、续写人类精神。
「真正的写作契机,是出于对自然生态的忧虑」
记者:《雪山大地》以高票获选第11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杨志军:当然是意料之外,但也似乎是意料之中。坦白说,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没有那种强烈的念头——我一定要得奖,完全没有。
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者是不能考虑太多的,也不会考虑太多的。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自己的情感得以抒发、想法得以呈现、自我得以安放。很多时候,这是情不自禁的,不能有功利目的。
既然是自己用心血凝聚而成的作品,我就有这份自信,它是一部好的作品,可以为读者带来裨益。所以,创作时没有想获不获奖的事,获奖了却也不感到十分意外。
记者:您这种不得不写的强烈情绪,最初是从何而来的?
杨志军: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读书,收藏了很多文学作品。即使是在那个“不能读书、不让读书”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出版的中外小说,我们家几乎都有。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只能去父母的书架上找东西看。那时,我读《安娜·卡列尼娜》,根本读不懂,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只知道书里的人在谈恋爱。《水浒传》是我重要的启蒙读物,但同样看不懂,甚至连很多字都不认识,只知道一大帮人在打架。当然,书中很多人物的那种仗义疏财的做派,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童年时期接触文学作品,对我日后走上写作道路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能说是我的写作契机。真正的契机出现在我在陕西省军区当兵的时候。那阵子,我被派到生产队进行支援,每天的饭是挨家挨户去农民家里吃的,这让我近距离接触到了农民的具体生活。有一回,我在等老乡做饭时发现他家有本破书,里面有一篇小说,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看完后我想,哎呀,这样的小说我也可以写的!从此之后,我走上了写小说的路。
我年少时写的一些小说,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但即使发表了,我内心也没把它们算作我的作品——那时候写的东西,无论是语言还是技巧,都实在不太好。我自认为我正式的文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在上大学以后。我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参加高考的,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在那里读书时,我遇到了很多让我一生受益的好老师,也因为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所以老师们对我们格外上心与爱护。老师们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学养教会了我许多,我的思路被打开了。老师们并不是照本宣科地纯粹从结构、语言等技巧方面来教我们写作,而是结合他们自己丰富的经历让我们去了解文学、文人,去触摸文心。
毕业后,我回到青海日报工作。有一次,一些农民因大风吹裂了青海湖的冰面而被困在浮冰上,我去现场采访。当时,除了完成新闻稿之外,基于这段亲身经历与见闻,我还写成了《大湖断裂》,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随着采访中积累的环保知识越来越丰富,我又写了《环湖崩溃》。
那时候的文坛,主流是伤痕文学,当大家几乎都在回顾历史、创作伤痕文学时,我独自在关注生态向度的社会问题。这或许是受我的工作的影响,作为记者,我每天在接触现实,尤其是西部的现实,亲眼看到很多破坏生态的现象——比如在生态本就脆弱的草原上盲目开垦耕地,等等。因此,说到底,我写作的真正的、重要的契机,是我对自然生态的忧虑。
「悲悯心和责任感成为此生写作的底色」
记者:历经数十年,您的文学创作一直聚焦于生态题材,体现您对生态的关切,《雪山大地》也是。
杨志军:对,我一直是这样的。这个与我的天性有关系,我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也觉得人在大自然面前绝对是渺小的。
牧民对待自然是十分敬畏的,而且,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信仰。比如对于一座山,如果外来者为了挖矿而把草除掉、把山刨开,牧民是很反感的。他们觉得山是有灵性的,是神山,是不能乱挖的,挖山就像剖开人的皮肤、伤及人的血肉,神山是会因为受损而发怒的。因为牧民有这样朴素的信仰,所以,青藏高原的生态长久以来维持得比较好。我在老百姓家住的时候,观察到他们居住在临近水源的地方,但并不会直接将衣物、用品拿到河中洗。他们会在河边挖一个坑,然后用水桶一桶桶地将河水运到大坑中去洗,因为他们觉得河水是圣洁的,有神明居住其中,人怎么可以直接在河里洗衣物而把河水弄脏或打扰神明呢?
他们不管是取水还是做其他事,都是需要多少取用多少,绝不会出于贪念而肆意夺取。就像挖药材,如果牧民今天只需要用一株,他看到那里长着三株,他只会取一株,而让另外两株或继续生长或留给别人用。因为这是大地母亲的慈悲馈赠,取用就一定是用在所需之处,不能浪费也不能多占。
我还特别喜欢动物,这也让我更热爱自然、更关注生态。我养过很多动物,狗、红嘴鸭,等等。在藏区,人和动物的关系比其他很多地方更为亲密。我曾经写过《藏獒》,藏獒在许多牧民家里是家庭成员一样的存在,会得到相当的爱护。虽然牧民也会为了生存而宰杀、食用牛羊,但他们宰杀牛羊前都会特别伤感,会请别人帮忙宰杀自家的牛羊,并且是要念经超度它们的。
在《雪山大地》里,雪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父亲,大地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母亲;雪山的雪水滋养着大地上的生灵,大地使得生灵有栖息之所。这是一种生态上的和谐。总之,生态是我写作中的重要关切。西方现当代也有一些生态主义小说,但和我们的生态书写还是有些不同的;这和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自然、和谐、节制观念是我们古代文化中非常宝贵的部分,当代人应当从中有所汲取。
记者:离开藏区之后,您主要生活在青岛,创作了不少带有明显青岛特点的作品。青岛和藏区,两种不同的地理空间,对您的文学写作和精神生活产生了什么样不同的影响?
杨志军:影响肯定是不同的。首先青藏地区和青岛地区的自然景观、文化属性是很不同的。就自然景观来说,青藏高原多是雪山、草地,而青岛有着十分广阔壮美的海洋景观。
就我本人而言,虽然我现在生活在青岛,但我是在藏区长大的,我眼中和我笔下的青岛更多是我以一种“草原人”而非都市人的角度观察到的青岛。可能与雪山大地、与藏区文化带给我的悲悯情怀有关,我天真地希望通过作品来补益都市人的精神缺憾。比如,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寄希望于音乐对人的救赎与治愈,在《最后的农民工》中则希望农民工的奉献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他们身上那种天然的淳朴与善良是都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市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本身就具备很强的文化吸纳能力,我用作品致敬都市,是因为它给了我很多思考人生和思考生活的机会。我希望我的文学能从辽阔的雪山草原延伸到同样辽阔的海洋都市,延伸出一种新的文学思考和精神追求。
总之,藏区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带给我的悲悯和责任感,成为我此生写作的底色。在和青岛的朋友们交往时,他们可以感受到我身上的藏区文化特质以及这种特质和青岛文化、海洋文化间的碰撞,但这种碰撞带来的更多是益处而非矛盾,这就很奇妙了。
另外,青藏高原的辽阔博大和青岛大海的辽阔博大都在我的写作中得以呈现,尤其是景物描写,更是重要的呈现。如果把我作品中描写景物的片段汇集起来,那也会是一本厚厚的书。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