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以下简称《商贸与文明》)之后,日前,历史学者张笑宇推出了他的“文明三部曲”收官之作——《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
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所说:“技术是引擎,商贸是黏合剂,产业是硬实力,终造成现代文明的宏伟大厦。”“文明三部曲”的视野广阔,观点新颖,是解读“现代文明”的钥匙。
在《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中,张笑宇以“产业”为楔子,以复杂社会为观察对象,进而为理解当下的世界与社会打开了全新的视界。
对复杂社会的理解不到位,容易触发它的崩溃
记者:我们都知道社会是复杂的,而在《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以下简称《产业与文明》)中,您首先希望读者理解的就是“复杂社会”的概念,为什么?
张笑宇:《产业与文明》中的“复杂社会”这个概念不是我们日常用语说的“人心险恶、社会复杂”那个“复杂”,而是有两个学理来源,一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复杂系统”,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复杂社会系统”。
前一个意义可以参考杰弗里·韦斯特的《规模》这本书,这本书里说:“蚁群的建筑事先没有筹划,没有得到任何个体观念、集体讨论或磋商的帮助,也没有蓝图或总体规划,只是成千上万只蚂蚁在黑暗中无意识地工作,将数以百万计的沙土颗粒搬来,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结构。”这就是简单逻辑经过规模累加形成复杂系统的机理。而后一个意义可以参考约瑟夫·泰恩特的《复杂社会的崩溃》,这本书里说:“一个社会在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既定层次上出现快速的、实质性的衰败,它就已经崩溃……崩溃又必须是快速的——不长于几十年——而且必须伴随社会政治结构的实质性衰败。”我引用这两本书的内容讨论这个概念,是想表达两个意思:第一,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它是由简单逻辑组成的,但不能用简单逻辑去理解。现行的很多理论观点、历史理解、意识形态都是简单逻辑,不足以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复杂工业社会。第二,复杂社会的效率虽然高,但也有快速崩溃的风险。如果我们对复杂社会的理解不到位,就很容易触发它的崩溃。
记者:在我们这样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文明阶段,您在三部曲中对于人类过去文明的探索有怎样的意义呢?
张笑宇:人类对任何领域的探索都不外乎一个根本,就是寻找因果联系。如果我们相信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机的、虚无的,而是有规律的、有逻辑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去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寻找因果联系的过程中,如果你的解释框架只限于当下,而不能溯及以往,那你找到的因果联系当然就是没有解释力的。
我们探索过去的文明,不是说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过去,而是用今天更加完善的因果关系理论框架去思考过去。人类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物种,社会学规律的底层是物理学规律,包括能量汲取、物质交换、资源分配这些。这些底层规律当然不会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因此,结合历史上我们能收集到的数据讨论这些变量与人类文明的因果联系,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如您所说,处在复杂的社会之中,我们的未来又会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张笑宇:书里的最后一章讨论,复杂工业社会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历史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升了巨大的效率,但它本身是存在地缘政治前提的。如今这个地缘政治前提正在瓦解,意外冲突频发,这是有可能造成复杂社会崩溃,造成“正增长秩序”停滞的。我想这个风险现在不仅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且还在逐渐成长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人还在关心全球化时期的中心议题,比如投资增长,比如投资技术进步,我想这些方向对社会的改善效力正在快速衰减,恐怕下一个时代我们要讨论其他方向上的议题了。
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会带来高增长
记者:您在《产业与文明》中提到,“90%的技术出不了科学家的实验室,都被人们遗忘了”。那么,怎样让有用的技术不会被“锁死”在实验室里?
张笑宇:具体哪些技术能通过检验,我们是无法预知的。站在1700年,我们想不到是铁锅的普及帮助了坩埚技术和冶炼技术的发展,从而为发明蒸汽机奠定了基础。站在1800年,我们想不到是煤矿运输的需求帮助了蒸汽机车渡过早期的“尴尬阶段”,持续取得盈利,最终造就了伟大的铁路系统。站在1850年,我们想不到是颜料工业推动了化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大规模生产药剂、化肥、化纤,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站在1990年,我们想不到是电子游戏产业推动了芯片的发展,最终在2010年前后造就了人工智能的大爆发。这一切路径都是自由发展的,是不可能预知、提前计划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让消费需求更兴旺发达,让商业环境更友好便利,这样科技创新企业才能更容易存活下来,赚取更多利润,反哺到研究部门去。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本质上要靠共同富裕。
记者:能够被我们记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通过了一个漏斗的筛选和检验;通过了漏斗检验的技术,可能会反过来使社会生活、生产产生巨大的颠覆性的变化,就像喇叭放大声音一样,所以您创造了一个“漏斗—喇叭”模型。这个“漏斗—喇叭”模型非常形象,您是怎么想到这样去形容发明研究与生产力的?
张笑宇:这是我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简单总结。2015年前后我曾加入过一些创新公司,当时在电子消费产品领域有一个200元定律,就是说早期的一些电子消费品,像手环、智能音箱这些,功能还很简陋。第一代消费者是把它当作玩具购买的,不追求实用性。但是如果你有了第一代用户,你可以赚到钱,你就可能改善产品的技术和使用体验,让它变成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产品。
很多电子消费品,当时看都以为会改变时代,但是最终那些公司、那些品牌都没有成功,被淘汰掉了。所有人都知道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但是好像反过来又以为技术总能改变社会。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一者是微观视角,一者是宏观视角,技术改变社会其实是宏观视角下的幸存者偏差问题。用“漏斗—喇叭”理论把宏观、微观连接起来,你就明白这背后的机理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提这个理论的用意。
记者:技术是功利性的,它可能为民造福,也可能导致“礼崩乐坏”。它如何维护“正增长秩序”,又如何破坏“正增长秩序”?
张笑宇:技术进步有时在宏观上都不一定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说现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TFP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表现出来的。它是扣除了资本、人力要素投入之后的生产率,它反映由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取得的效率提升。那么我们看到,二次工业革命成果在美国,足足贡献了50年的TFP高增长,从1920年持续到1970年。而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对TFP的增长贡献只持续了8年,而且水平还更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二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延长供应链的技术进步。汽车、电视、冰箱、电灯、电话……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产品,每一个新产品背后可能有几家大公司和几百上千家上游供应商,背后又是成百上千万的新工作岗位。它令整个社会更加富裕,消费能力更强,从而推动新技术更容易通过“漏斗”的检验,再度转化为产业。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自动化技术是缩短供应链的技术进步。原先由工人生产的,现在给机器人生产了。造成的结果是就业不足,竞争压力增大,消费萎缩,这就是很多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的状况。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进行了很多产业转移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工作。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简单思维理解复杂工业社会,以为增长可以是线性的、无限的,技术进步永远会带来高增长。复杂工业社会的运作法则不是这样的。
记者:人工智能、机器人蓬勃发展,这本来是技术进步,是“正增长秩序”的产物。但也会让社会产生大量被“甩出去”的失败者,让社会进入病态,动摇“正增长秩序”的根基。在您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笑宇:我们看2009年以来的深度学习,还有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它们其实都在快速取代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它不是取代蓝领,而是取代白领。比如深度学习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电话客服方面,我们知道这是门槛最低的脑力劳动岗位之一,曾经容纳的就业是很多的,但是现在都被淘汰了。现在以ChatGPT、StableDiffusion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我一直在使用。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替翻译、助理、绘图师、剪辑方面的初级脑力工作。它当然还代替不了凡·高或者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天才,但是当它能够3分钟画一幅凡·高仿作的时候,当斯皮尔伯格原先需要300人团队,现在只需要30人团队的时候,它当然就对就业市场和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
我觉得中国尤其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人口规模摆在那里,就业压力摆在那里。增长如果不能充分转化成就业,这个当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这个技术的负面影响对我们可能会比对很多其他国家来得更猛烈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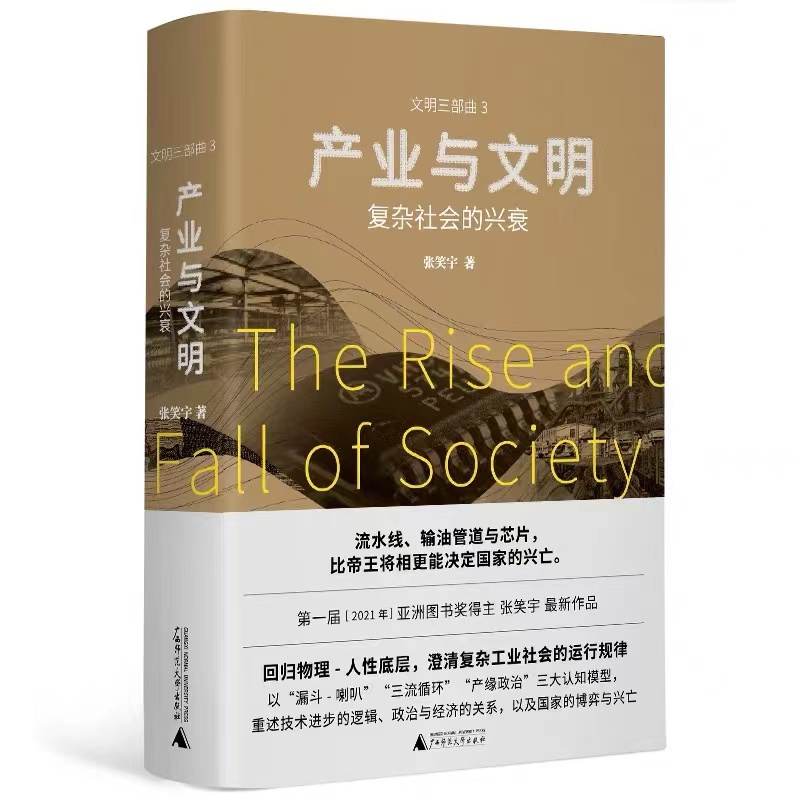
《产业与文明:复杂社会的兴衰》
张笑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