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销美食作家、多项写作大奖获得者扶霞·邓洛普爱上中国美食,已经30年了。
她一直把介绍中国美食视作自己的“人生使命”,试图回答,中国菜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餐、如何吃中餐?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如何真正地欣赏中国美食?
在她的新作《君幸食: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她如此总结: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本文摘自该书。
谷粮天赐:白米饭
一顿中餐,首先要有“饭”,再加“菜”(粤语里称之为“餸”),菜也就是“除了饭之外的其他所有东西”。汉字“菜”可以指一盘盘的菜肴,也可以是蔬菜。看这个字的构造,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采集的采,像一只手放在草木上。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中,大部分中国人,“除了饭之外的其他所有东西”,主要就是蔬菜,因此“菜”这个字眼就有了一定的逻辑。最简单的菜,可能就是那么一盘韭菜炒豆干,甚至一碟好吃的咸菜;最复杂的菜,能包含无数佳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成。
然而,无论菜肴多么美味奢华,终极目的都是搭配主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下饭”。在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些中国省份,人们通常不说“菜”,直接称为“下饭”。用美国人类学家文思理的话说,饭是中国人饮食的“核心”,而菜(或称“下饭”)则是“边角”。而且,正如其他文化中的淀粉类主食一样,“核心食物的口味有时一尝之下显得平淡单调或千篇一律,与当地人通常对它的虔诚崇敬形成鲜明对照”。正如我的英国父亲要是几顿没吃亲切而抚慰人心的土豆,就会如同没见到亲人一样怅然若失,大部分的中国南方人要是吃不到米饭,就会倍感凄凉。没有配饭吃的食物,只能说是小吃,不能算正餐。
日常的一餐,主要是大量的饭,佐以少量的菜;而到了宴席上,两种角色就会完全反转,享乐重于温饱。菜品数量激增,可能会到令人应接不暇的程度;而淀粉含量高的米饭则成为小角色,小到几乎没有戏份,甚至也许会由几个小小的饺子或一个袖珍小碗的面条代为出场。但米饭绝不会完全消失: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一场盛宴上吃完二十多道菜,解脱与胜利的感觉正慢慢充溢心间时,就会有好心的服务员来到身边,问我要不要吃点米饭、包子或面条来填一填。没有饭,就不能称其为一顿正宗的中餐。所以,很多中国人即便在吃完一顿丰盛的英式烤牛肉配蔬菜,再品尝了甜品布丁之后,仅仅过了半小时,就会嚷嚷自己还饿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举动像一面镜子,神奇地映照出西方人对中餐的态度。
“饭”,可以指任何做熟的谷物,但谷物也有传统的等级之分。南方人最喜欢的是大米,而北方人则更喜欢能做饺子、面条、煎饼和馒头的小麦。穷人和边远地区吃得比较多的所谓“粗粮”或“杂粮”,比如玉米、高粱和燕麦,整体上则不那么受欢迎。这个“谷物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土豆和红薯等淀粉含量高的块茎类食物,通常只在饥荒或极度贫困的情况下才作主食。一个绍兴的三轮车夫曾给我讲述过他贫穷的童年,他那时候老吃土豆。我告诉他,英国人觉得土豆是美味可口、非常不错的主食。他表示难以置信。“天啊!”他带着一脸关切与担忧地说。
一个人对“饭”的态度,能多少说明其为人如何。家常便餐中,要是有人只顾大口吃菜,不怎么吃饭,就会显得有些贪嘴。中国最著名的美食家、18世纪的诗人袁枚曾曰:“饭者,百味之本……往往见富贵人家,讲菜不讲饭,逐末忘本,真为可笑。”千古礼仪典范——圣人孔夫子,即便面前有很多肉,也绝不吃超过主食比例的量。饭在中餐中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让以社交为目的之一的用餐活动变得非常灵活:只要锅里还有足够的米饭,即便突然又来一位客人,你也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这顿饭就再多吃一会儿。
万物可入菜:选择食材
该怎么来定义何为“食材”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达成一致意见,就是食材必须能食用。但哪些东西可食用呢?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主观了,要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来回答。典型的英国人可能会认为腐坏发臭的(蓝纹)奶酪可食用,但这东西会吓坏很多中国人;同时,英国人看到法国人特别喜欢的蜗牛和青蛙腿,也会觉得过于可怖。对于“这个能吃吗”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纵观中国历史,“食材”这个概念,其实不怎么基于规则,而更基于可能性。在作物歉收或饥荒的时候,知道哪些野菜可以吃,穷人就抓住了救命稻草。而富人将丰富多彩的食材视作饮食乐趣的一部分,越是出人意料、标新立异,越是喜闻乐见。
有的东西本身就是完美的食材,比如11月的大闸蟹,或是春天第一批最柔嫩的竹笋。但即便那些被很多人弃之如敝屣、粗糙而残缺的东西,也能在某时某刻找到用武之地:重点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处理它。
所有的食材都有自己的特质,无论其优点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中餐厨师的职责就是不要因为种种缺陷而否定它们,而是要认真审视它们的特质,看看如何能通过各种创造将它们的特质发挥出来。举个浅显的例子:如果要做弹嫩多汁的白煮鸡,那么很多筋骨的老母鸡显然不合适,但它能熬煮上等的高汤,那可比一只丰腴肥嫩的童子鸡合适多了。动植物的大多数部位都是有可取之处的。就拿柚子瓤来说,无色无味,如同棉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作食材的潜力。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厨师的技艺、创造力和想象力。
也许,最能代表英国的菜肴就是烤肉配土豆和蔬菜,每一样配料的烹饪方式都简单直接,上桌后也基本保持原形,一目了然。要是英国厨师手里没有熟悉的食材,那就麻烦了。海蜇可不能单烤,柚子瓤也不可能单煮。但中餐就不一样了,其本质就是转变,是混合与搭配,是让不同的食材达成圆满的大和谐。中餐这个体系中涵盖的技术和方法,可以应用于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浓淡相宜:中式调味
中国人重视清淡的菜,部分原因是他们讲究以食作药,认为均衡饮食对保持健康至关重要。不过,推崇朴素的食物也涉及文化与道德因素。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在《淡之颂》一书中陈述种种有力观点,表示“清淡”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不仅表现在烹饪中,更体现在音乐、绘画和诗歌艺术中,因为中国人并不认为“清淡”是缺失了什么或有什么不足,而是某种“源点”。他说,中国人根深蒂固地爱着含糊、暗喻与写意,无论是水墨画中氤氲消融的山水,还是消隐于无声的音符或“无味”之味,都一脉相承。“清淡”并非虚无,而是对万事万物可能性的一种升华。
中国古代祭祀时“喂养”神灵,要用无味的羹汤,而智者则应不受浓烈的风味与刺激的美食这些身外小事所惑。“五味”带来的兴奋只会蒙蔽人的判断力,正如道家经典《道德经》中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古代中国圣贤的超凡之处,就在于能拨开周遭世界感官的迷雾,感知到纯粹与精华,能在无味之中悟道,以克制保持感官的敏锐与活力。
如今,很多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正被越来越多的诱惑所吸引,远离清淡菜肴所代表的“浮世清欢”。他们越来越爱吃味道夸张的食物,比如那些“鲜味炸弹”般的菜肴,那些用油和辣椒填出来的食物,要卖相好、可上镜,被鸡精与味精疯狂提味,让唇舌享受到刺激的快感。也许是因为大型工业化养殖场提供的肉与反季蔬菜缺乏了灵魂“本味”,没有了好的食材,不怎么调味的菜肴吃起来就像刷锅水。也有可能是人们太累、太疲倦了,迫切渴望能通过进食迅速刺激味蕾。或者,这只是饱和市场上疯狂商业竞争酿成的苦果,一片内卷之中,声量越大的味道,越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但如果不感受安静、平和与清淡的乐趣,只有酸甜苦辣这些重口味的刺激,就无法充分领略中国美食的魅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清淡的菜肴就是艺术品的留白,可以起到衬托与突出的作用。狂野的味觉刺激,需要清淡的菜肴来进行必要的调整,恢复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静和。各位也许以为,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中国舌头”的那一刻,是发现自己喜欢上了鸡爪和海蜇,其实不是。我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白粥和水煮蔬菜,和对糖醋鱼、麻婆豆腐一样喜欢,这才是我心中真正“中国化”的表现。
要是只吃美味和刺激的菜肴,你也许是在吃“中国食物”,但并非真正在品尝“中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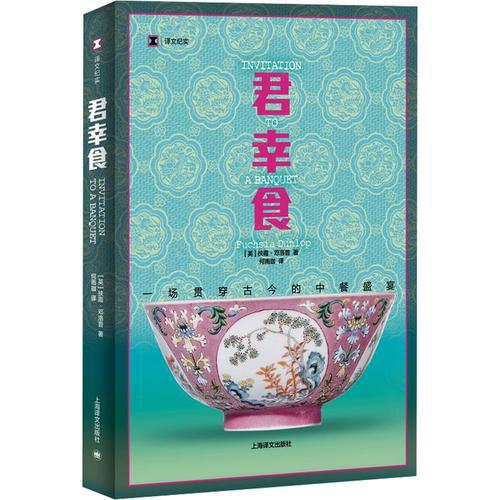
《君幸食: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
转载请注明出处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 在外国人眼中,中餐有多好吃,他们如何吃中餐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