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认识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石。由蔡丰明、程洁、毕旭玲撰写的《上海城市民俗史》一书,对民俗文化研究有所突破,展现了文化关照新视野。
长期以来,我国民俗学被认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即缺乏学科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典籍中可以看到,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民俗学思想,诸如《山海经》中体现的民俗地域性文化述说,《周易》中的文化形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论述,都是一些从地域性角度阐述民俗思想的体现。特别是《周礼》,更显示了文化与地域、人群互动所形成的个性差异。这些典籍都是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基础。汉代末年又出现了应劭的《风俗通义》,更体现了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标志着我国民俗学理论趋于体系性与完整性。
近年来,民俗研究进入新境界,特别是城市民俗与乡村民俗的并重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在当代社会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如何融入多元性的工业性成果,如何使社会发展更健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民俗研究成为学术探索的特殊命题。
《上海城市民俗史》所展现的,是一种历史文化研究的典型,具有“走进历史”和“走出历史”的双重性。这部专著从上海城市的早期形成入手,深入论述了“城”与“市”的发展与关系问题,并把晚清时期作为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也成为了上海城市民俗形成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海的城市构成与中原不同,与欧亚同体的边疆也不同,它是从东方渔村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租界的设立而成为国际都市的一个特别的地域。其实,大航海时代并没有特别直接地影响上海的形成,直接促成上海城市格局形成的是晚清时期,即1840年这一裂变时间与空间的交会,算是大航海的遗迹体现。
阅读本书,会想起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晚清之前的福建人陈振龙,是他从远方带来红薯,成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另一个是晚清时期的福建人陈季同,是他首先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大地。前者可视为文化输入,后者可视为文化输出,这两种现象在上海这一城市中有着典型的汇集。书中特别提到了租界对世界的融入与移民对国内各地的融入而构成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基点问题。历史存在偶然,也存在必然,历史造就了上海,也造就了具有海派特色的上海城市民俗。“以人为中心”这个命题在此更准确地表现出历史的深刻性与完整性。
《上海城市民俗史》在阐述上海的特殊性的同时,也分析了上海城市民俗的现代性。现代性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现代所对峙的就是传统,上海的衣食住行皆与传统形成差异,体现出上海民与俗的文化个性。书中特别提到上海民俗在现代历史上不同阶段所呈现的更具特殊性的问题,更全面、广泛地揭示民俗与时代的特殊联系。比如,不同的党派在此相遇。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这里传播,尤其是上海工人起义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无产阶级政权在上海建立,继而推动全国社会发展。
上海城市工业化、商业化是上海城市民俗的典型。在中国社会现实发展中,上海城市文化与城镇化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前沿,成为中国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典型。本专著将文化的颠覆作为着眼点,具体阐述了文化的转化、裂变及其所构成的城市民俗,这是对我们今天提倡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命题的具体诠释。这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性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何把握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如何破除陈旧的思想文化观念,如何创造新的文化观念。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又要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这是我们的文化立场。这部著作正是在这些方面启发我们深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时期再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上海城市民俗的特点及相关研究,是该书的写作难点。在这一部分,作者的论述非常突出“变化”,破旧立新成为新上海城市民俗的主题,即以新风尚与新思想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这在全国具有引领意义。上海的文化具有开拓性,更具有国际性,已成为上海城市民俗研究的新命题。当然,书中也阐述了上海城市民俗的两重性,如上海人一方面具有开拓包容的精神、海纳百川的性情,另一方面又有人把所有外地人皆视为上海以外的“乡下人”(即不开化、不文明者)。另外如上海城市民俗具有更多的移民色彩问题,讨论起来更复杂,也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总之,这部专著作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成果,充分体现了拓展性和严谨性,把文化、文明、文艺诸因素都纳入了上海民俗的考察视野中,深入阐述了上海的“海”和文化的“化”,展现了上海民众的文化塑造力和上海民俗强盛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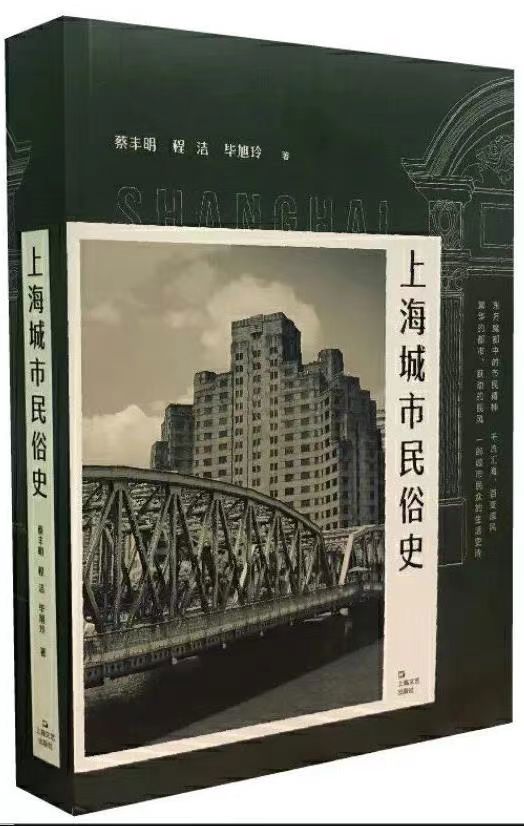 《上海城市民俗史》,蔡丰明、程洁、毕旭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城市民俗史》,蔡丰明、程洁、毕旭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