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服的历史不仅限于过去,也关于现在与未来,关乎我们如何一路走来,形成了今日之经济、思想和道德状态。”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索威尔在《征服与文化:一部世界史》(以下简称《征服与文化》)一书中所写的话。
的确,“征服”是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话题。从远古时期的部落争斗,到诸如罗马这样的“普世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乃至近代的帝国主义殖民活动,都充满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征服”活动。甚至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史上最畅销的即时战略游戏系列也名曰《命令与征服》。
本书是托马斯·索威尔15年研究和旅行的成果。在讲述重大历史事件发展进程的同时,作者还从征服对世界经济、军事、政治格局,对民族命运和社会,甚至对人类生物学的改变做了详细阐释,并呈现了这些改变对文化的冲击与再造,以及对人类生活的重塑。
几乎所有族群都卷入过征服的浪潮
索威尔在这本书中提到,“几乎所有族群都卷入征服的浪潮,或是征服别人,或是被别人征服,这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此,首要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有些族群能够征服别人,而另一些族群却只能被征服呢?在这方面,《征服与文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譬如,在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时,索威尔就认为当地“各种地理条件都不利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甚至有扼杀性的影响”。其结果就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尽管是人类的发源地,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却远远落后于旧大陆的其他区域。就算是西非历史上黑人原住民最后的帝国桑海,其面积也只勉强相当于法国,而这已经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历史上“巨无霸”一般的存在了。至于美洲的古老文明,情况也有类似之处:“缺少驮运畜力构成了远距离文化交流的一个更普遍的阻碍”——大约只有驯化了羊驼的印加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
实事求是地说,《征服与文化》中关于文明受地理条件影响的论述,容易令人联想到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里的相关描述。其中原因其实倒也不难理解,对于英文原版问世于1998年的《征服与文化》一书而言,索威尔在写作时参考戴蒙德的最新力作是必然的事情,书中甚至还直接引用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新西兰毛利人征服同文同种的查塔姆莫里奥里人的片段。
多年前,一方面显得《征服与文化》里的一些数据丧失了时效性,譬如在谈到前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人口时候出现了“八千多万”这个数字,而实际上这个非洲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两亿大关……另一方面,倒也使得索维尔不必过于顾及在新千年西方知识界的“政治正确”风气。书中提到,“非洲黑人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异族征服,一种是家园被占领,另一种是在外大批为奴”。而与惯常叙事不一样的是,《征服与文化》里指出,“征服和奴役它们的既有其他非洲人,也有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贩来的奴隶比欧洲在西半球的海外领地更多”。反倒是19世纪的“英国对世界自由的一个更大的贡献或许在于摧毁了国际奴隶贸易,进而终结了奴隶制”。这是因为,“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让它有能力强令很多主权国家接受废奴的法令”。这番论述自然有替英国美化之嫌,毕竟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活动中英国也曾是个活跃玩家。但索威尔之所以这么说,或许仍然与其特殊身份有关——他自己就是非洲裔美国人,还是个不多见的保守主义者,并以对自由派黑人民权人士的尖刻、讽刺批评而闻名。
征服带来的影响广泛且深远
至于《征服与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实不在于征服的“原因”,而在于征服的“后果”。索威尔当然承认,“自古以来,征服一直靠的是主动施加暴行和蓄意营造系统性的恐怖”,大多伴随着“令人胆寒的惨剧”。
但索威尔同样指出,“征服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当时发生的悲惨事件上,更多的是对后世的持久影响”“征服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广泛且深远的,其后果是文化的、制度的、生物的”。实际上,《征服与文化》全书通过对四个群体——英国人、非洲人、斯拉夫人和西半球印第安人的分析,用来说明更先进的文化征服了不太先进的文化时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后果。
在关于英国的描述里,读者便同时看到了积极与消极后果的存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前后被英格兰征服,境遇却截然不同。一方面,“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知识界的大师中有相当多是苏格兰人或苏格兰人后裔”,譬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或是发明(改良)蒸汽机的瓦特,“在18世纪下半叶的黄金时代,苏格兰知识分子群体走在了欧洲各个文明的前沿”。爱尔兰的情况却截然相反,19世纪早期,爱尔兰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9岁,而当时美国的奴隶的平均寿命也有36岁。“美国奴隶的饮食也要丰盛些,甚至有劣质肉吃,而爱尔兰人以土豆为食,偶尔能吃上鱼,一年到头可能都见不到一点儿肉。”
征服在其他地方的后果倒也没有如此反差剧烈。比如沙皇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当然将当地民族置于从属地位,反而是外来的“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族统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欧洲文明的思想、产品、技术、实践也因此传入中亚,使得“中亚民族因为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有所交流,获得了经济发展、医疗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收益,当然也付出了代价”。这也正是索威尔所说的,“有些征服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被征服族群的后代得以生活在祖辈不曾想象的,有更多的可能性的世界里”。
“人力资本”可以决定征服后果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征服的消极后果呢?对此,索威尔在书中提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经济文化交往的区域范围与多元性,它不仅决定了社会的经济水平,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培养技能、获得知识和广泛接触文化的过程,这些被统称为‘人力资本’。”一个民族保有的“‘人力资本’往往比现存物质财富、自然资源和个体才能更能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在索威尔看来,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寡,决定了征服后的不同命运。“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外国援助了大量实物和资金,却没能推动经济发展,就因为当地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同样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仍然“允许外国人在经济中充当重要的角色”,保留了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因此其经济走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而好于原本较为富裕的加纳与尼日利亚,就是一个“人力资本”决定征服后果的例子。
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提升族群的“人力资本”?“一个显然的情形是,残暴的征服往往与广泛的技能传播相伴。”《征服与文化》列举了波兰人的例子。“在美国的波兰移民中,来自普鲁士者普遍掌握各类手艺技能,因为几百年前日耳曼人征服了普鲁士,这些人一直生活在普鲁士文化中。相比之下,来自波兰本土的波兰人就较少掌握这些技能。”在二战后的非洲,非殖民化“变革之风”的引领者大多是接受过西方国家正规教育的“西方化黑人精英”,正是因为这些人组成了本地的“人力资本”。
毋庸讳言,关于“人力资本”与“征服”后果两者的关系,是《征服与文化》的创见之一。当然,增加“人力资本”并不见得只能依靠“征服”这一个方式。譬如书中也提到,“在俄罗斯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国民大多不识字,因此人力资本也十分匮乏”。但沙皇俄国并不是别国的殖民地(反而通过领土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做法是“倚重外部力量”。“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全欧洲招揽科学家、手工匠人和各种生产型人才,让他们来发展沙皇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并不是没有效果的——“俄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某些领域取得一点儿经济进步,就会体现为绝对产量的大幅增加”。
为众人的探索和讨论打开视野
《征服与文化》里的相关叙述,不免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征服的后果,纯粹是被征服民族自我抉择的结果,越顺从、适应征服者的新体制,就越容易在双向接触中取得“人力资本”,因此也就能在“后征服时代”取得成功。这一点似乎有其局限性。就拿书中提到的北美洲印第安人“五大部落”(奇克索人、切罗基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以及塞米诺尔人)来说,因其对待欧裔移民的态度较为友善,亦吸收了较多他们的文化而得“文明”之名,但在19世纪初,美国的白人持有这种观点:土地在那里是让人去开发利用的,美洲原住民没有完全利用好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白人有权利用好它。183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迁移法》。随后的10年里,大约125000名美洲原住民在美国军队的驱赶下被迫迁移到了荒凉贫瘠的西部平原。的确,“能否获得欧洲的武器以及与欧洲人联盟成了决定印第安人战事成败的关键因素”,西迁后的“五大部落”毕竟掌握了更好的武器,因此“在西部过得比当地的大平原印第安人还要富足”。只不过,按书中给出的统计数字,1990年时,切罗基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只相当于白人的69%。这能够称为“成功”吗?
另外,从历史上看,征服者有时候甚至刻意阻止“人力资本”的转移。譬如在19世纪初,经历了拿破仑的短暂入侵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进行了改革,由于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中最先进的地区。马克思曾称赞阿里是奥斯曼帝国中“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可惜阿里的成功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警觉,阿里的改革事业最终半途而废……
从“五大部落”与穆罕默德·阿里的例子看,如何在征服的条件下成功积累“人力资本”,实在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可惜,《征服与文化》述不及此。或许托马斯·索威尔本也无此野心,他的著作“无意为民族和文化这样宏大的课题下定论,相反是要抛砖引玉,为众人的探索和讨论打开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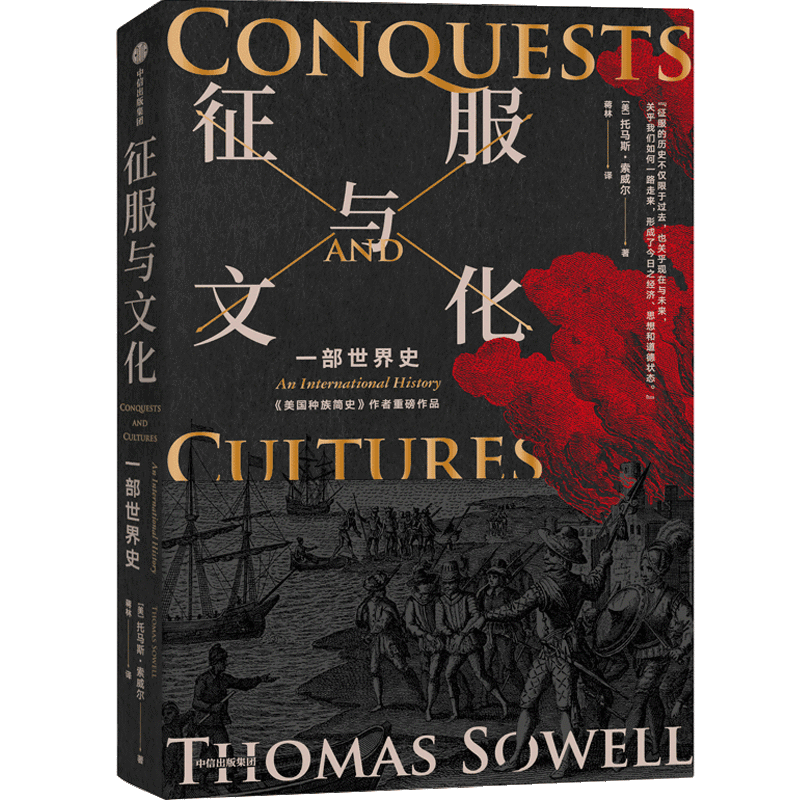
《征服与文化:一部世界史》
[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