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维护和平为目的而出现的制裁武器本身却源自一种战争实践,作为集体安全的执行手段而实施的封锁措施最终却催化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经济制裁的制度性悖论,也是20世纪初期的理想主义国际政治家们政治抱负的落空。两次世界大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初具雏形,其背后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两大特点:一是拥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规范;二是国家间、不同政治体间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图景。而这两个特点是和经济制裁的制度化进程同步发展,相互塑造的。
在现代,经济制裁发动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现代国际规范依赖精密的审计和统计系统发挥作用,因此负责设计和执行经济制裁的精英靠钢笔和书桌就导致了战间期近10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国联的设计者伍德罗·威尔逊在见识过制裁的威力后,也感叹道:“封锁比战争更可怕。”这也许与其血液中的战争因子相关。毕竟,在发明之初,制裁就是一种战争工具,其目的是对敌人进行威慑,通过对物资匮乏的恐惧屈服敌人的意志。
在《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一书中,康奈尔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尼古拉斯·穆德回顾了经济制裁是如何从战争手段变成“和平卫士”,最终又是如何意外地造成大量非战人员的损伤,甚至将世界更快地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制裁武器实际上并不新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希腊人就通过自己的海上优势对敌人的城市和村庄进行封锁,通过截断物资给敌人带来物质和心理的双重伤害。但是国际层面的大规模封锁,是在19世纪末高度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上实现的。
一方面,工业革命后技术的革新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和交通系统的发展。铁路、邮轮让全球范围内的物质交换成为可能。为了实现更大的生产规模,欧洲国家不仅开拓了远在南美洲的原材料产地,而且在当地建立了银行,通过殖民地和宗主国间的汇款,以及欧洲国家间的银行拆借和融资,新兴的国际公司得以最大效率地操纵时间和空间,赚取利润。
与全球物质交换系统同时出现的是发达的国际金融系统。人员、商品、资金的流动在和平时期变成统计数字,在战时则变成配额。发达的全球金融系统转变了国际规则发挥作用的方式。以锰矿石为例,德国当时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钢铁生产国,每年消耗世界锰矿石产量的四分之一,但其原材料库存仅能维持两个月的生产需要。制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效用让国际主义者对制裁的威慑力更加确信。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后,随着物质逐渐繁荣,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出现了。以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为代表,欧洲的精英认为,随着国家间贸易往来逐渐密切,国际贸易网络逐渐复杂,商业文明将带来和平与全球秩序。这是因为任何理性的行为体都会发现,战争并不能带来更多利益,反而会给全部参与者造成损失。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种贸易和平论的缺陷,但是贸易和平论者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念,他们反而支持把国家分为进入商业文明的“现代国家”和不遵循商业文明规律的“野蛮国家”。安吉尔认为,应该把制裁作为一种强制执行工具,通过经济压力迫使“野蛮国家”服从国际秩序,从而让国际关系进入贸易和平状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伍德罗·威尔逊等国际主义者倡导建立维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国联,并把经济制裁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执行手段。
从自身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国联总共进行了三次制裁:针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针对希特勒的德国以及针对侵华的日本。这三次制裁均以失败告终,并且每次制裁带来的心理恐惧都让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未雨绸缪,争相展开自给自足运动,并对外发动侵略。从这个角度来看,制裁反而导致了矛盾的螺旋上升,最终让国联和修正主义国家陷入制裁和自给自足的恶性循环,并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线。
制裁带来的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及其导致的矛盾的螺旋上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的物质繁荣也被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大萧条极大程度地摧毁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逐渐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主导让制裁成为比之前频度更高、烈度更低的常规实践。我们不应该只从狭隘的经济视角看待制裁,而应对经济制裁背后的规范性意涵保持警惕。同时,历史经验证明,制裁不能成为结构性国际矛盾的解决措施。理解制裁背后的制度逻辑及其政治意图才是有价值的。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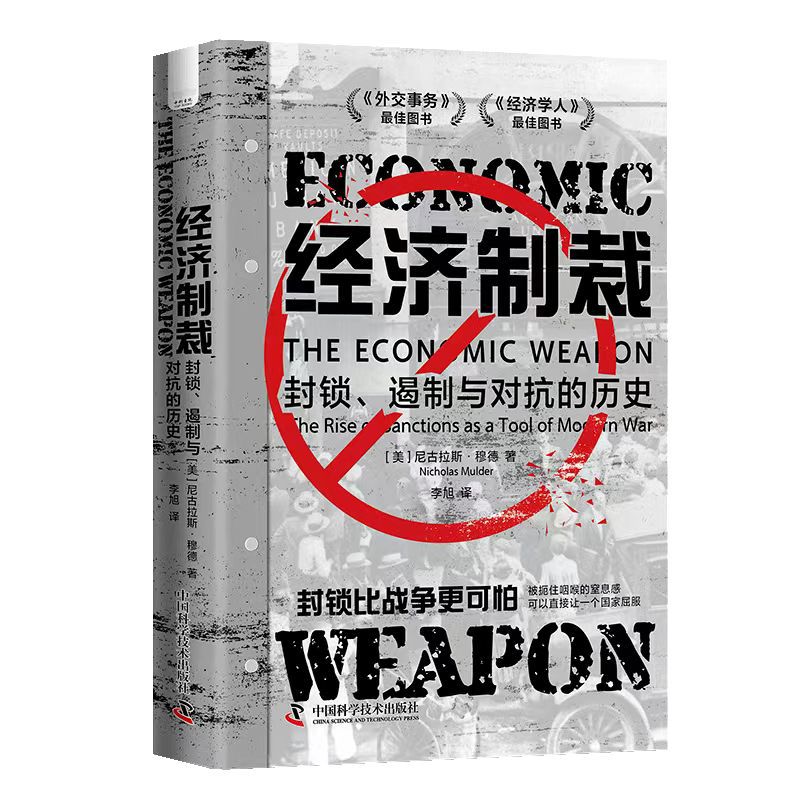
《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
转载请注明出处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 历史经验证明,制裁不能成为结构性国际矛盾的解决措施,经济制裁,防止战争还是引发冲突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