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畅销书《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道金斯的大名已经无须多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道金斯以冷峻的思考与缜密的逻辑展开关于“人”的讨论。“自私”这一颇具道德意味与伦理判断的词语所表达的意义,只是基因的“本意”:保存自我。这种对“自我”的忠诚,铸就了基因的“自私”,也显示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自私的本能面前,“表现真诚无私的利他行为的能力”是人类拥有的非凡的特征。这显示出作为“生命”的“人”的多维与丰富,更彰显出基因的秘密是如此的诱人和无尽。
正是因此,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已经让他声名远播的时候,依然笔耕不辍,写出了他更为看重的《延伸的表型》。
破题尝试
在《自私的基因》的第13章,道金斯就展开了关于“基因的延伸”的讨论,并将《延伸的表型》称之为“职业生涯的最高成就”,因为后者直面了前作遗留的难题——“生命”与基因之间的矛盾:生命体可以是一架精密运转的机器,在基因的操纵之下完成传递基因的任务;与此同时,“如果失去了基因的角度,生命体便失去了繁衍的成功率”。概言之,“生命”与基因之间的矛盾,犹如“鸡生蛋,蛋生鸡”的选择:何者为先,都有所依据,但谁做决定,也均有理由。可以说,《自私的基因》用基因完成了对“生命”的祛魅,但并未化解“生命”的矛盾,这也成为写作《延伸的表型》的直接原因。
阅读《延伸的表型》并非易事:层峦叠嶂般的生物学概念、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时不时出现的数学运算……随便拉出一样,都能让非专业人士失去耐心。已经著作等身、声名远播的道金斯,一定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仍要如此行文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他深知自己面对的问题是多么严苛与重要,若不动用真能耐、苦下笨功夫,势必无功而返。从书名的确定便可见一斑:相较于“自私的基因”这样极具辨识度与吸引力的标题,“延伸的表型”无疑更具学术性与严肃性。作为传统遗传学的标志性概念,“表型”指的是基因作用在生命体上的显现特征,“延伸”指的是这种特征由生命体自身扩展到生命体之间,比如寄生虫对宿主行为的控制、生物对无生命世界的操纵等等。道金斯以“延伸的表型”为切口,希望对“生命”、生命体行为以及生命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延伸的表型”作为对“生命”与基因之间难题的回应,着眼于二者之间的中介“生命体”:一方面,“生命体”既是“生命”的赋形,也是基因的显现,无论是生命的活力与朝气,还是基因的运转与传递,都需要通过“生命体”的具体行为获得彰显;另一方面,“生命体”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纳为基因的运作,但生命体之间的合作、友爱、团结、争执……若只能概括为“自私的基因”,那“生命”的多彩又要从何谈起呢?为此,“延伸的表型”在基因的立足点上,着眼于生命体多姿多彩的行为,在行为中探索基因的作用,在基因中寻找行为的秘密,以“延伸”的无尽,将生物学的研究深化为思想的实验。
无尽“延伸”
“思想实验”是道金斯生物学研究的独特之处,更是深刻所在。一方面,它有悖于生物学的科学性,因为生物学对于实验数据、测试结果的倚重,强调实证的重要,“思想实验”这种暧昧不明确的概念,似乎与生物学的学科特性有所错位;另一方面,“思想实验”开拓的讨论空间,恰好激活了实证在想象力与思想力上的谨慎,促成了生物学面向“生命”时的沉思:用基因廓清“生命”的秘密,用思想深掘“生命”的意义。
“思想实验”作为道金斯阐释“延伸的表型”的方法,巧妙之处体现于用递推的逻辑,将基因的“表型”作用“延伸”为生命体自身、生命体之间以及“远距离作用”三个方面,以步步为营的思想力量,达到“重新发现生物体”的目的,最终完成对“生命”的再认识。
首先,在生命体自身,基因的“表型”作用体现为遗传演化,比如河狸在河流上建筑水坝的行为,就是基因遗传的体现。道金斯的巧妙之处在于省略了对基因本身的深究,转向对遗传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注,强调“只有当水坝在基因控制下发生变化时,这一切才会发生”。发生的“一切”,均是“表型”作用的彰显。
其次,在生命体之间,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关系,也让基因的表型得以显现。道金斯以吸虫对蜗牛壳厚度的改变为例,说明吸虫的基因对蜗牛的影响,这种影响让蜗牛与吸虫处于共享的关系:“蜗牛壳表型就是一种共有的表型,受吸虫基因和蜗牛基因的影响。”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道金斯特意强调了他的思维与一般生物学研究的不同:寄生并不意味着两种生命体基因之间的“竞争”甚至“胜出”,而是隐含着生命体之间的“共有”或“共享”。即使这种“生死与共”的生命关系会表现得甚为残酷,但想到这是“自私的基因”所致,也就变得合情合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死生契阔的联系,成为“延伸的表型”的最佳注脚,即“‘延伸的表型’延伸到这些基因所在的细胞外,延伸到其他生命体的活组织里”。关于“远距离作用”的论述,便是对这个“注脚”所做的更为精致且深入的论述。
总之,从生命体自身的遗传作用直到生命体之间的“远距离作用”,基因的“表型”在道金斯的论述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延伸”。无尽的“延伸”,让生命体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联结,在“共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生命”的意义更新。
在《延伸的表型》的第1章,道金斯就点明了对于生物学研究中过于关注“个体躯体”的不满,他并不认为“生命”是“离散生物个体的集合”,“延伸的表型效应”让他意识到生命体之间存在“共同命运”与“共同动机”,这直接让生命体之间拥有着“共享的命运”,“这些独立、有个体追求的载体经常组成群体,个体生命被紧紧捆绑于其中,正如狼群和蜂群一般”。对于基因的锚定,尤其是对于“自私的基因”的关注,让他明确生命的生物学本质是“复制因子的战场,它们互相摩擦、争夺、战斗,以争取基因的未来”;“思维实验”的思想力量,让他将生物学的发现深化为对“生命”的意义更新,即“生命世界可以被看作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复制因子效力场所组成的网络”。
“网络”的定位,不仅回应了“延伸”的发现,更让“生命”在道金斯的笔下拥有了独树一帜的面貌。由此反观生物学,道金斯实现了对“生物体”的“重新发现”:在“延伸的表型”的理论视域之下,“生物体”不再是离散孤零的“个体躯体”或完全被基因控制的“运载工具”,而是“与单一生命周期相联系的实体单位”,它在时间与环境的考验中演进、更新、变化,以完成“自我保存”的目标。但这又已经不同于“自私的基因”的石破天惊,而是以更为朴素与恳切的方式,完成对“生命”的意义探究与价值肯定。
生命循环
从“自私的基因”到“自我保存”,“延伸的表型”让“生命”在意义的层面获得深化与更新。在道金斯的笔下,“生命”的“过程”充满坎坷与挑战,他称之为“瓶颈”。“瓶颈”对于“生命”的作用,体现在对“生命循环”的促成。但这又并非圈内的故步自封,而是生命体之间生生不息的延续,即“只要现存的生物已经繁殖,而新一代的循环再次开始,那么前一次循环也就可以结束了”。这种“生命循环”,让生物学的“思想实验”充满了诗意与感性,也让人有感于生命的韧性与顽强,更让“自私的基因”在冷峻深刻的同时,拥有着更为动人的情感张力。
正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到的那样,“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父与子”的伦理赓续让“人”超然于其他生物;“生命循环”则让“人”重返为“生物体”,并且在“生命”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自己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醒出“共生”的重要性:这并非理论的一厢情愿,而是“生命”的应有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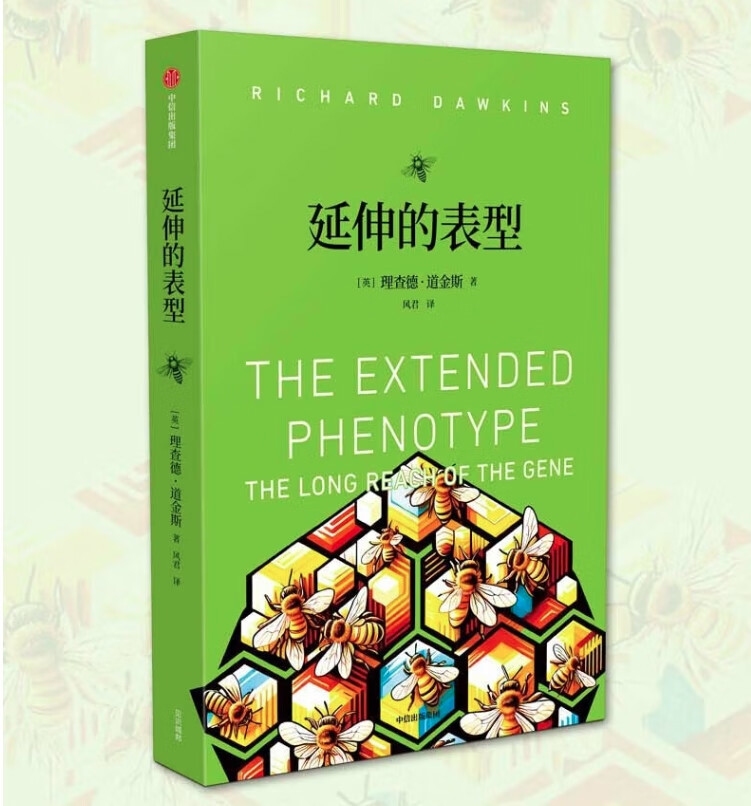
《延伸的表型》
[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风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