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曾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在将来的某一天,开一家小小的书屋,店长本人只需偶尔去淘些好书,大部分时间则可以窝在角落安静看书。这种将读书作为职业,不必沦为社畜的生活想必十分惬意。
作家顾真也有这样的梦想,不仅如此,他还切切实实付出了行动——他在家附近的周末集市摆起了书摊。虽然这次尝试并不成功,但他依然将开书店作为理想职业:“如果没有当作家,我会是个书商,在柜台后面把其他作家做的梦和为生活开出的良方卖给大家。”
下文摘选自《书会说话》,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您对朋友有什么要求?”
“首先,不能蠢。”
英格兰格罗斯特郡书商斯图尔特在旧书堆里爬梳了大半辈子,版本熟烂,又通装订,写出一册《藏书入门》,见识、趣味俱在。
《初版书及其问题》一篇尤其好玩:“一个收藏者如果一根筋买初版书,那用不着花多少钱就能把书架塞满。书籍的初版本不一定像大众以为的那样价格不菲。世上多的是初版书,因为一本书就算毫无价值,也有它的初版本。”
四十多年过去,市场翻覆,文章里那些古椠珍本的价格已成历史,但热衷此道者的心态并无改变:“理智的藏家不会什么初版初印都要,而是搜求那些他怀有特殊感情的作品,藉此拉近与心爱作家的距离———后来的印次或许更完美,却毕竟不是一本书最初问世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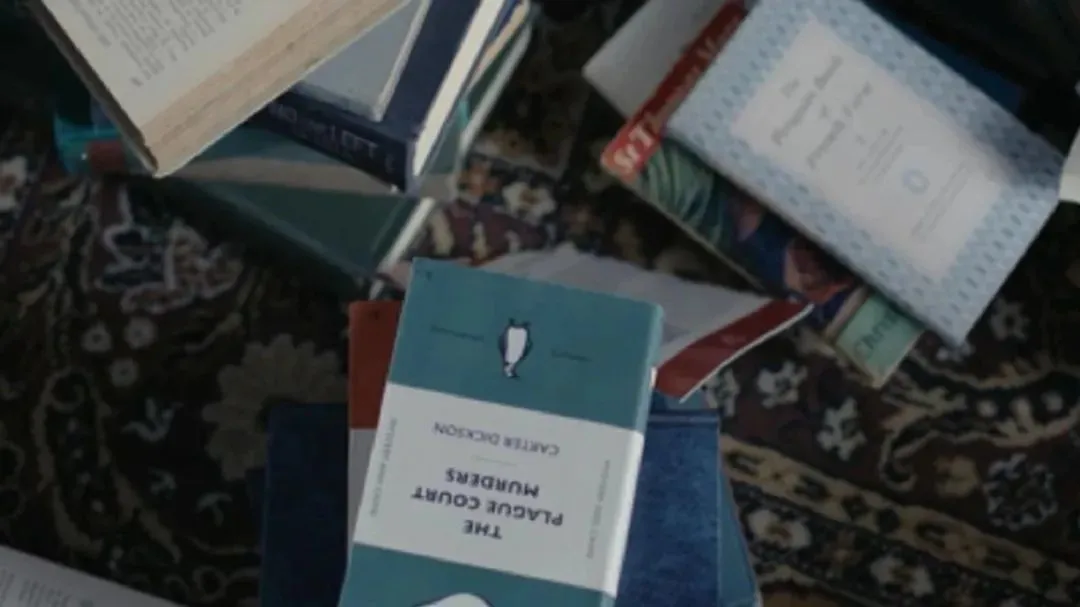
那日与一位收藏毛姆经年的好友闲聊,问起她搜罗初版书的初衷。
她的回答很简单:“当然是为了读啊。”
都是《刀锋》,一本是海涅曼的英国初版,一本是新印的“佳酿版”平装,读起来有没有不同?
看来,有的。
二十世纪英美文学名家名作的初版在旧书市场上向来走俏,我想要的沃尔夫、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都贵,都要不起。想不到前两天竟误打误撞淘到一册英国初版《蒂凡尼的早餐》,黑灰两色护封包裹大红书壳,一道花饰分开书名作者名,封底是杜鲁门·卡波蒂的速写像和简介。
与更为常见的兰登书屋美国版不同,此书的英国版并不在版权页上标明印次。翻阅卡波蒂的书信,我们只能看到他对美国版的反应。
收到贝内特·瑟夫寄来的样书时,他正在希腊。当地警察还差点把书当成了海洛因。卡波蒂很认可书的制作与设计,而兰登书屋版的《蒂凡尼的早餐》也如预期般畅销,重印了好几次。但英国初版显然没这么好的运道,查遍旧书网,在售的寥寥无几,倒因此更见稀缺了。
译文社的前辈说卡波蒂是天才,文字沾了魔力,句句可诵,《蒂凡尼的早餐》开头漂亮极了,百读不厌。卡波蒂晚年在《为变色龙奏乐》的前言里说,“蒂凡尼”为他写作生涯第二周期画上了句号。
这部小长篇成书前,原定在1958年的夏天由《哈泼市集》刊出,可临到发表,同卡波蒂私交不错的编辑卡梅尔·斯诺被解雇了,新编辑认为小说过于下流,决定不予刊登。最终这部作品出现在了《时尚先生》上。卡波蒂自此同《哈泼市集》绝交:“再给他们登?哼,上他们门口吐痰我还嫌脏呢!”
藏书说到底藏的是故事。 集藏初版书,是想寻进深巷,坐在古宅门口的矮凳上听当事人细数前尘梦影。哪怕回忆靠不住,掺进了好恶糅进了想象,也比局外人的二手编派来得有温度。
《蒂凡尼的早餐》出版后,评论界褒贬不一。
卡波蒂的老相识威廉·戈扬在《纽约时报书评版》撰文指责作者始终活在自己“矫揉造作”的小说世界里。恼火的卡波蒂在给朋友的信里直接说,“酸葡萄心理”害戈扬精神变态了。
可十七年后,戈扬的太太居然写信请卡波蒂为她丈夫小说的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写推介文字———若不是脸皮厚,只能说是太健忘。
卡波蒂回信道:“麻烦请您丈夫回忆下当年他是如何评价《蒂凡尼的早餐》的,到时您就会明白,您的来信有多么荒唐。”
戈扬夫妇大概没看过卡波蒂1972年的访谈《自画像》,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您对朋友有什么要求?”
卡波蒂答道:“首先,不能蠢。”
02
“为什么没人收藏我呢?”
常逛旧书网站AbeBooks的人,想必看熟了那句广告语:Passion for Books。又简洁又清亮,每次打开网页,不禁要默念上一遍。多年前在校园流动书摊上翻到一册书话汇编,名字也叫《为书燃情》,哈罗德·拉比诺维茨和罗伯·卡普兰编,当即买下。
周末居家无事,拣出闲读。前言就气象不凡,到底是雷·布拉德伯里的手笔。这位《华氏451》的作者自剖心迹道:“构成我过往的皆是书,鲜有其他”,“我生命中的女人无非图书馆员、语文教师和书商……我总是渴望受教育,而枕边私语最合我意。”
《为书燃情》辑录了古今关于书籍的近六十篇文字,有完整的篇什也有零散的段落。浏览目录,只见星光熠熠:瓦尔特·本雅明、翁贝托·埃科、苏珊·桑塔格、福楼拜、弥尔顿,等等。不少是久已读过的名篇。 也有相对冷门作 者的文章,“集锦”中收录的这部分作品或许更能见出编者的眼光与匠心。
罗伯特·本奇利的《为什么没人收藏我呢?》便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篇。
此文是针对“失去理智”的藏书界而作。
本奇利愤愤不平,为何同为作家,他的老朋友海明威的初版书能走俏市场,而自己的不管是绝版书还是签名本都乏人问津,只能待在旧书店蒙尘,“初版的古登堡《圣经》值钱,这我知道;或者,谁若有机会摸到作者签名本《坎特伯雷故事》,那也不妨当一回雅贼,可看到欧内斯特的初版书变得那么金贵,我不光吃惊,还隐隐有些沮丧”。
他想不通,“我这个人和我写的书到底哪里同收藏者合不来啦?我英俊非凡,一口流利的法语,在文章里还能不时抖几个法语词儿……可我的名医朋友说,病人出院时会把不要的书留在医院,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的作品”,“明明我比海明威年纪大,写得还比他多!”

本奇利一边发牢骚一边自嘲一边讲了海明威为他题写签名本的两段往事。
第一次是给仅仅印了一百七十册的初版《在我们的时代里》题签,本利奇强调,他请海明威签名只是不想再听他唠唠叨叨讲打猎的奇遇了,“我费了好大劲才跟他解释清楚,我不是仰慕他的作品才请他签字,主要是想看看他究竟会不会拼写”。
第二次轮到《永别了,武器》,海明威“毁书毁上了瘾,硬要亲手把那些被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人用破折号代替的‘污言秽语’一个一个重新填充进去”。 他在扉页上的题词是:
E.(———).H.给R.(G).B.
修正版。空格填满。
非常珍贵。有销路。
罗伯特·本奇利一度是相当活跃的幽默作家,常给《纽约客》写戏剧评论,自己也演戏,无怪乎文笔毒辣。
《为什么没人收藏我呢?》最先发表在1934年(第五卷)第二期的书迷刊物《科洛丰》上,而海明威生于1899年,彼时的他,已经写出好几部传世之作。一个年仅三十多岁的青年作家,初版书已如此受人追捧,放到今天有点难以想象。
那么,本奇利文章中提到的那版《在我们的时代里》如今到底市价几何呢?
在AbeBooks上检索了下,最低价格在四万美元上下。再查查看本奇利的第一本书Of All Things———不特别讲究品相的话,花三十美元就能买到一册了。
03
“真正的读书人少之又少”
一
毛姆写过一篇小说,叫《书袋》,主人公是个嗜书成瘾的作家,在一次东南亚旅行中,他带了一个巨大的亚麻布袋子,里头装满了他可以根据不同场合和心境拿出来阅读的书籍,“袋子重达一吨,压得脚夫们站都站不稳”。
派驻当地的代理公使接待了他,还热心组局打了桥牌。其中一位牌友沉默寡言,引起了作家浓厚的兴趣,他再三向代理公使询问后,听到了一个比装在书袋里的传奇更为精彩的故事。
肖恩·白塞尔当然没有拖着书袋四处旅行,这位坐拥十万藏书的二手书商正守着“书城”威格敦的书店,等待好故事上门来。
因为开书店,他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客人 :声音忧郁、每次打电话来都要找十八世纪的神学书却从来不买的威尔士“女人”;拿自制手杖来换取购物积点、倾心苏格兰民间传说的“文身控”桑迪;写信文句不通却自以为是、非要来当图书节嘉宾的所谓作家;身患阿尔兹海默症、明明可以网购却始终支持实体书店的迪肯先生。
肖恩是电子阅读器(他店里最著名的装饰便是一台被猎枪射碎屏幕的Kindle)的坚定反对者———毛姆如果活到今天,单凭这一点,或许也愿意同他喝上一杯,他老人家怕是不会指望笔下的人物对着一位手持Kindle的作家袒露心扉。
肖恩是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的老板,出版于2017年的《书店日记》记录了他从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的开店经历。肖恩的店名丝毫不会引起歧义,直接就叫“书店”,可即便如此,还是有顾客来问:“你们该不是卖书的吧?”
每个月日记的开篇放了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BookshopMemories)中的一段。
奥威尔此文写于1936年,回忆他一边写作《叶兰在空中飞舞》一边当书店店员的经历。在他的经验里,“真正的读书人少之又少”,来光顾书店的多数是“不太能被证明的精神病人”。肖恩对此心有戚戚:
《书店回忆》里的记述放到今天依然真实,对于幼稚如我者更是逆耳的忠告:
别以为二手书商的世界是一曲田园牧歌———炉火烧得很旺,你坐在扶手椅上,搁起穿着拖鞋的脚,一边抽烟斗一边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与此同时,络绎不绝往来的客人个个谈吐非凡,在掏出大把钞票买单前还要同你来一段充满智慧的交谈。
真实情况简直可以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最贴切的评论或许还要数奥威尔那句“上门来的许多人不管跑到哪里都是讨人厌的那一类,只不过书店给了他们特别的机会表现”。(《书店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页)
《书店日记》的读者大概很难不被他犀利的言辞逗笑,不仅光顾书店(往往只看不买)的客人是他的吐槽对象,店员、活动嘉宾、书商同行都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不过,他并不承认自己天生脾气差,自辩说:“记得在买下这家书店前,我还挺温顺友善的。连珠炮似的无聊问题,朝不保夕的资金状况,与店员和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讨价还价的顾客漫无休止的争论,害我成了这副模样。”

每篇日记的前后清楚记录了网店订单、每日流水和到店顾客的数据,让我们在满屏毒舌中汲取慰藉心灵的养分之时,也看到了二手书业惨淡的现状。
其实“书店”的财务状况应该已经是业内相对健康的了,可即便如此,如今的肖恩也雇不起全职店员。
二
旧日的爱书人去大小书店或者冷摊上淘书的过程,其实是买家卖家间一场知识的角力。网络固然让搜罗心仪的旧书变得空前便捷,却也无可逆转地扼杀了披沙拣金的雅趣。藏书大家A.S.W.罗森巴哈在《谈旧书》一文中生动地回忆过他的书商舅舅摩西。
听闻外甥也想走边藏书边卖书的道路,摩西舅舅认为他完全具备资质:
记性好、毅力强、品位佳、文学知识丰富、拥有一定资金。这几条是前网络时代当一名合格书商的基本要求。
确实,过去的书商往往是学有所长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时有书志学著述行世。哪怕是肖恩刚买下书店的2001年,还会有亦商亦儒的高人对他指点一二,如今这代人已凋零殆尽。
《书店日记》中写到的戴维是老一辈书商的代表,令肖恩高山仰止:
在亚马逊和AbeBooks这些你可以很快核查书价的网站尚未出现的年代,书商必须掌握和携带所有信息,而戴维是一座人物生平、目录学和文学知识的宝库。
如今这种知识———倾注大半辈子心血积累、曾经那样为人所珍视、可以藉此谋得体面生活的知识———几乎没了用处。
那种看一眼封皮就能告诉你出版年份、出版社、作者和该书价值的书商难得一遇,而且数量在日渐减少。我依然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行家,他们是我在这行中最为钦佩的人。(《书店日记》,42页)
旧书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神奇魅力,罗森巴哈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佳本汇集之处,自会透出一股神秘气息与难以捉摸的美感,让整个空间染上异色。
这样的观点也许不算荒谬吧: 并不是看过同样的内容,就称得上看过“同一本书”的。 1865年麦克米伦初版《爱丽丝漫游仙境》和当下印行的“企鹅版”黑皮经典,即便内容与插图几乎一样,根本不是同一本书。
每一册旧书都独一无二,参差的“书品”下藏着一段甚至几段历史,后人很难确切知道新入手的旧书曾经身在何处,归何人所有,却也不能说毫无蛛丝马迹可循,有时是页边笔记,有时是藏书票,有时是夹存的老照片、老剪报,“书本来源的隐秘历史让许多人兴奋不已,点燃了他们的想象”。
三
一直很佩服那些敢于将自己的书架一览无余向外界展示的人,怯弱如我,总觉得这么一来,会被某双经验老到的眼睛看出书主人性格中的阴暗面。
对书痴来说,自己的藏书和本人之间已经难以分割;夜阑人静坐在书房里,看着架子上的一道道书脊,有时难免会想:如果某天此身化作尘土,这些书的命运将会如何?
卡里埃尔在与埃科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吴雅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我可以想象,我太太和女儿将卖掉我的全部或部分藏书,用来付清遗产税等等。这个想法并不悲哀,恰恰相反:旧书重返市场,彼此分散,到别的地方,给别的人带来喜悦,激发别的收藏热情。”
很潇洒,很豁达,如果他不是在逞强的话。
《书店日记》中最引人感伤的当属肖恩去新近过世的人家里收书的部分,随着主人离开人世,那些映射着他的人格,甚至可以被视作他存在过的证据的书籍也将流入旧书店,迎接未知的命运。

作为二手书商的肖恩常常要以处理遗物的方式同素不相识的亡故者告别: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你会渐渐对此感到麻木,尤其像今天这种情况:去世的老夫妻没有子女。不知何故,墙上的照片———丈夫穿着挺括的RAF(英国皇家空军)制服,妻子则是个游览巴黎的少妇———会带给人某种愁绪,而在处理尚有子女在人世的过世夫妇的旧藏时则没有这种感觉。
带走这样一批藏书好比是对他们人格毁灭性的最后一击———是你抹去了他们存在过的最后一点证据。这个女人的藏书表明了她是什么样的人:她的兴趣爱好同她本人的密切关系不逊于她遗传下来的基因特征。(《书店日记》,38页)
相信很多爱书人都有开书店的梦想,或者说,幻想。 作为个体户,肖恩自然有着令上班族艳羡的自由。前一晚和朋友酩酊大醉,第二天尽可以睡到中午;只要店里有人看顾,随意同好友去山上骑行、去海里游泳;开车载着女朋友去古宅收书,顺便饱览湖光山色。
不仅如此。
除了任性而认真地经营着“书店”,让二手书业成为威格敦的经济支柱,肖恩还在家乡起着更多积极的作用:
为当地的展览拍摄宣传短片,尽心参与操办威格敦文学节,不遗余力反对唯利是图的开发商修建风力发电机农场破坏自然景观。
虽然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遭受着伤痛的折磨(“我的背都僵了”“我的背痛得要命”“我的背正嘎嘎作响,使不上劲”),肖恩依然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让这艘船沉掉。
这种生活比给别人打工不知道要好多少。 ”
四
瑞克·杰寇斯基在《托尔金的袍子》的开头交代了开启自己贩书生涯的契机:
当年还是穷学生的杰寇斯基想送女友圣诞礼物却囊中羞涩,只好心一横,把一星期前刚购藏的一套二十卷本《狄更斯全集》送去牛津的布莱克威尔书店,没想到换得的钱是自己买入这套书时价格的两倍。
这让他意识到,原来收藏旧书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兴趣,还能够获得不小的收益,最后索性连大学教授都不干了,成为职业珍本书商。
肖恩踏足二手书行业并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开端。
十八岁时,他回乡小住,第一次看到了当时还属于老书商约翰·卡特(与著名的书志学家、《藏书ABC》的作者同名同姓)的“书店”,向朋友预言,它一年之内必然倒闭。
十二年后,三十岁的肖恩兜兜转转找不到心仪工作,回乡看望父母时发现“书店”并未倒闭,但卡特年事已高,想找人接手。但肖恩一没资金,二没经验,对踏出第一步犹豫不决。
也许是在肖恩身上看到了书商的潜质,卡特先是怂恿面前的年轻人办理了银行贷款(“你用不着有钱———你以为银行是干吗用的?”),又热心地陪他去客人家里收书,传授他生意经。
2001年,肖恩成为了“书店”的老板,一直干到今天。个别客人不怀好意的祝愿———“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你还在”———并不能改变肖恩在全书结尾说出的事实:书店依然开着。
说起来,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开书店———好吧,是摆书摊。
大约两年前的一个周末,早上醒来,我突然决定弃文从商,把一部分藏书运到离家不远的周末集市,花两百块钱租下个市口不错的位置,唯我独尊地当起店老板来。
满以为凭我的独到品位和高冷姿态必然顾客盈门,结果一天下来,遇到最多的问题跟肖恩一样:“小伙子,请问厕所怎么走?”
书呢,一本也没卖出去,只好回去踏踏实实继续朝九晚五。
但即便遭遇了这样的挫败和耻辱,开书店依然是我心中的理想职业,正如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书人”文森特·斯塔雷特在自传《生在书店里》中说的那样:
“在书店里,我第一次认识了书籍的芳香,第一次读到了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的不朽作品,第一次隐约感受到了妒忌、钦佩和作家身份带来的悸动。如果没有当作家,我会是个书商,在柜台后面把其他作家做的梦和为生活开出的良方卖给大家。”

本文摘编自

《书会说话》
作者:顾真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4-4
转载请注明出处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 即便遭遇了挫败和耻辱,开书店仍是我心中的理想职业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