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马清水河》是一部“纸上还乡”的诚意之作。丰厚的知识储备与摇曳多姿的行文特点,让这本散文集兼具学术色彩和文学价值。
透过作者杨占武的书写,既能够看到厚重的寻根意识与人文情怀,也可以理解记忆的短暂与永恒。
记者:“在清水河畔,总是邂逅马的故事”,除了红军与马的故事,这片土地上还有过哪些“牧马”故事?
杨占武:在清水河流域,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为主,间事农作。游牧与农耕,都是顺应自然的方式。我在书里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在此仅举三个:
一是司马迁的记载。他在《史记》中讲过一个富豪的故事: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献给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包括牲畜,数量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区域——原州,不仅是官办马场的核心区域,还是陇右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马城”(养马基地)。约50年间,原州一地的牧马数量由3000余匹一举增长到70多万匹。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去灵州会见铁勒诸部时越过六盘山,特意视察了陇右监牧的牧马。安史之乱时,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办马场的数万匹军马,“军势稍振”。可以说,这里的战马曾经是庇护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马政的衰落。大致来看,有管理混乱、牧军逃匿等因素,也有当时北方气候由暖转冷、植被变迁、土地沙化等自然环境趋于恶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间盆地乃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不断被垦殖,黄土丘陵区开荒一直开到山顶上,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
这种生态教训,不得不引发对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思考。生态建设要从一棵树、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清水河流域发生历史性巨变。如今,宁夏南部地区生态建设日见成效,林草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阔山远的清水河,未来可期!
记者: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在农耕和游牧分界线两侧,还能打捞出其他历史“碎片”吗?
杨占武:书中收录的《青冈峡里韦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韦州是今天宁夏同心县的一个镇,政治、经济、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却以“州”为名。历史上,它曾是兵家必争之要道。北部为毛乌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东沙区”;过此地,就到达灵州,即今天的宁夏平原。《新唐书》说古老的丝绸之路“萧关通灵威路”,“威”即指韦州,军事意义、商贸价值都很突出。用“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韦州长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浑人、吐蕃人以及党项人,都视其为必争的膏腴之地。韦州也是距离沙漠最近处的一道“甜点”,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触角之一。唐皇室“和亲”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国王诺曷钵后,因为吐谷浑在与吐蕃人的战争中失败,唐朝遂顺势决定辟地安乐州(韦州),安置其部众,并以诺曷钵为刺史。
此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气质逐渐在韦州扎根,确保了文脉赓续、弦歌铮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语境下,这有着别样的重要意义。
「共鸣是最高的奖赏」
记者:有评论说,《牧马清水河》具有“历史的厚度、哲学的深度和经济学的尺度”。您怎么看?
杨占武: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不敢保证,但至少我愿意这样去写作。书写故乡的关键在于“懂”和“悟”,成为故乡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说变成一个“文明内部的发言人”。纷至沓来的学术研究,仅仅将人群、村落视为“田野”,很难说不是在以学术的方式反复“赏玩贫穷”。我的书写是对故乡的一份记录,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祈盼和怜悯。
《一口水窖的容量》《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捞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记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写“冬储层冰,夏收暴涨”,用以解决人畜饮水的水窖;《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写畜草资源的匮乏以及寻找畜草的艰难;《捞浪茅》写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粪以解决燃料。大家当然会从中读出生活的困顿,但贯穿创作始终的主要是历史的追问以及经济学意义上的评判。
在《寻草的释义和我的寻草生涯》的结尾,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苏格兰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亚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会留心辨认有没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别是,如果看见冰草、枝儿条、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这些最适宜的畜草,自己会迅速地产生执念甚至冲动:这样繁盛的草,装满一背篼岂不是太容易的吗?”
我曾与读者作过交流,一些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潜意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共鸣。我希望自己书写的这些记忆,无论其形态和意蕴如何变化,人们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故事。共鸣,是读者对我最高的奖赏。
记者:“纸上还乡”是不是也应尽量避免成为一种私人的感受或体验?
杨占武:“纸上还乡”不能变成“乡愁的乌托邦”。英国近代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录进《牧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风土为写作背景,也体现了这一逻辑。
文化,在风土上孕育。我推荐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这篇文章写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粝的风土、人们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风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黄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说节奏,是一种叫作“坚忍”或者“忍耐”的东西。
文学创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酝酿而诞生的,但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对生命作执着的意义追究,是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选择一种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体验,那写作的意义难免会大打折扣。写作只有与现实相遇、与世界邂逅,才显得弥足珍贵。如果不能观照现实、不能关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义就很可疑。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说过,只要是动人心魄又充满魔力的记忆,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对事实“挑肥拣瘦”。它所酝酿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历历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无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书写的记忆,无论其形态和意蕴如何变化,人们都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鸣,才能回应“挑肥拣瘦”的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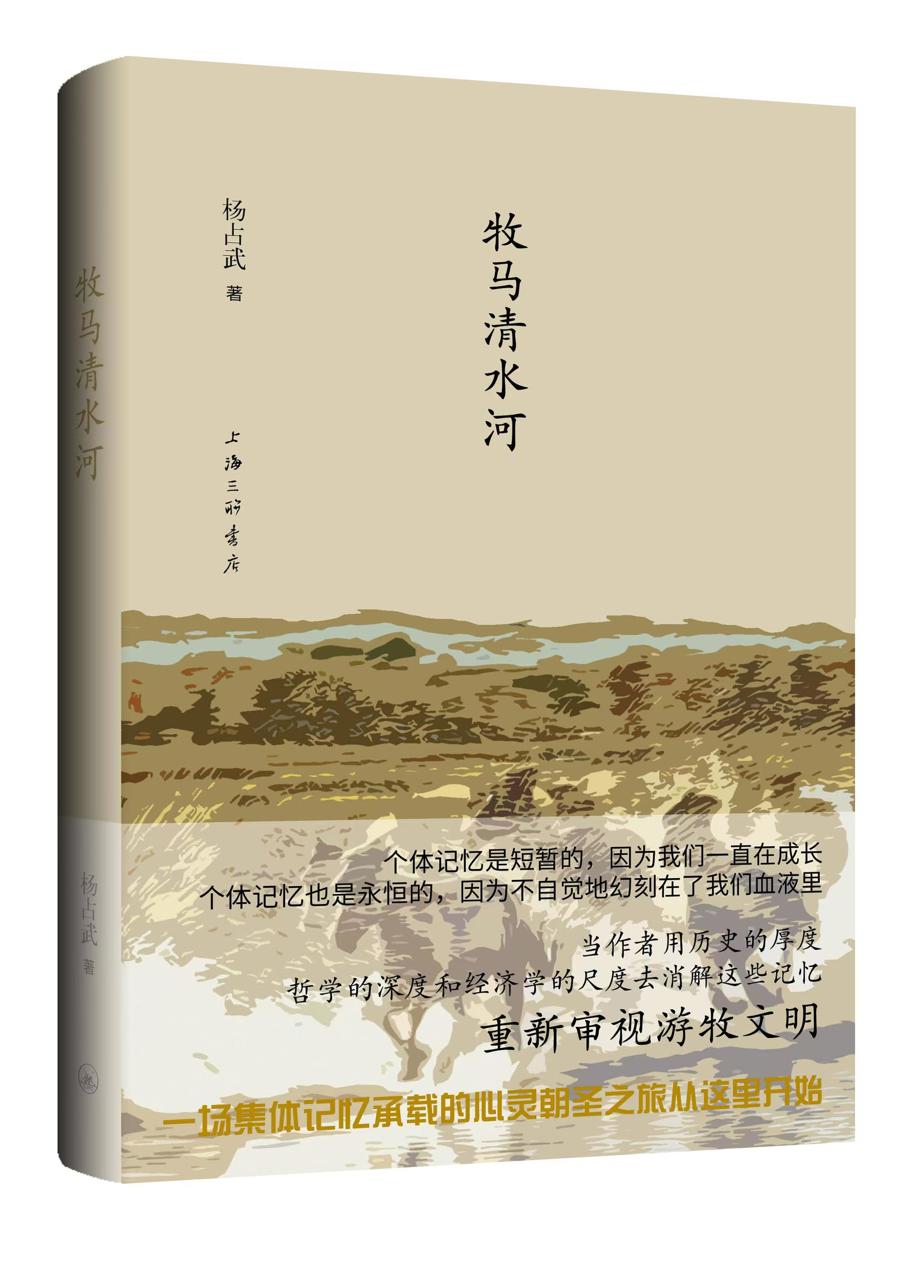 《牧马清水河》 杨占武 著
《牧马清水河》 杨占武 著
转载请注明出处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 《牧马清水河》:在农耕和游牧分界线两侧打捞“碎片”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华人站华人新闻,华人中文网
